|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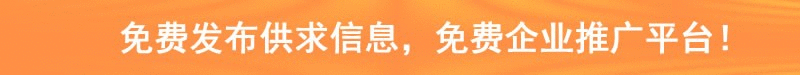
登陆享受更多浏览权限哟~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入驻经典 
x
编者按:12月15日,《向西而歌》新书发布暨西迁群雕揭幕仪式在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举行,20余万字的西迁人物传记《向西而歌》借助真实史实和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当年泰斗级医学前辈投身中国西部医学教育的珍贵场景。2019年,《当代党员》全媒体记者曾走访多位西迁前辈,还原了部分当年的故事。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烈反响,许多网友补充了不少关于西迁前辈的故事。今天,我们将这篇文章和这些评论整理出来,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动人故事。
1956年,18岁的朱朝君考上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报到那天下着小雨,她被一辆带篷的卡车从两路口拉到袁家岗。到了学校,她跳下车,看到教学楼还未修完,到处泥泞不堪,懊恼自己怎么考到了这所学校。
1959年,19岁的唐文渊坐火车抵达重庆菜园坝。出站后,他看到王家坡那片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心都凉了半截,不承想,重庆医学院的环境比这里更糟。当他置身于四周都是农田的学校时,失望的情绪在心里迅速蔓延开来。
1964年,20岁的吕长虹也坐火车到了菜园坝。他坐上3路电车(现403路公交车),一路颠簸来到重庆医学院。当这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提着铺盖卷和一只小行李箱踏进校门时,发现周围老师全说上海话,他有些恍惚,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朱朝君、唐文渊、吕长虹,分别是重庆医科大学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九届的学生。那时,刚刚踏进校门的他们,对即将就读的这所学校并不满意,是那群操着上海口音的老师,改变了他们对这所学校的看法。
“他们岂止是改变了我们对学校的看法,更是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走向。对于一代代重医学子和西南地区医学事业的发展来说,这些老师,就是燎原的火种啊!”吕长虹说。
拓荒的“耕牛”
记者采访时,已从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退休的吕长虹在整理旧物时,翻到一张老照片。
这是一张集体照,摄于1956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化学教研组欢送李韵笙副教授等赴渝教师的合影。
看着照片,吕长虹想起重医化学教研组教授朱传谨来重庆前,正是上医化学教研组的老师,于是便找机会把照片拿给朱传谨看。
86岁的朱传谨戴上老花镜,拿着照片仔细辨认,很快就在照片上找到了自己。
那是23岁的朱传谨,刚从上医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她穿着雪白的衬衫,留着短发,坐在第一排右起第三的位置。
正是这张老照片,将朱传谨的记忆带回到60多年前。
1955年,遵照****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将分迁至重庆。得到原卫生部关于迁院的指示后,上海第一医学院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并派出刘海旺、陶煦等一批教师和干部职工先行抵达重庆,开展建院工作。
1956年春天,朱传谨接到学院通知,她要和数十位老师一起前往重庆,承担首届重医学生的教学工作。
“学院安排我们去重庆,光是我们教研组就去了十几位老师。我那时很年轻,想到能够去重庆,投身西部建设,感到很高兴。”朱传谨说。
拍下那张合照后不久,朱传谨和同事们便告别了繁华的上海,登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他们溯江而上,在船上度过了漫长的八天,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来到周围全是农田、还在建设中的重庆医学院。
要从无到有建设一所医学院并不容易。从上海到重庆,这些西迁至重庆的老师们不仅工资降了一级,还要克服环境、教学、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建校初期,大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教学资源不足。”原重医基础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主任翁嘉颖教授曾回忆道:“当时,我们从上海带来的150具尸体不够用,为了开展实验,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们开始了艰难的‘寻尸’之路,打听到哪儿有腐烂的尸体就运回来埋掉,等尸体腐烂完毕就把尸骨消毒处理当教具。”
让朱传谨印象极深的还有,许多上医老师都是全家举迁到重庆。和她同船的物理教研组老师吕昌祥就带着他的四个小孩;带队的教务长陶煦身边,也跟着他的几个孩子。到了重庆,这些老师带着家人挤在宿舍楼里,起早贪黑,在开展高强度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入到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之中。
可即便是这样,也没人觉得苦,当时大家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
1958年,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传染病学家钱惪受组织委托,到重医担任副院长。那时,钱惪已经52岁,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带着家人迁到了重庆。
1996年,钱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400多位上医老师西迁重庆、建设和发展重医的岁月:“当初,我们是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建设而来。而今,可以说我们经受了锻炼,付出了辛苦,也看到了成果——学校、医院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辛劳在内,这几十年没有白过。”
创业的先驱
2017年2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心外科主治医师王小文跟随科室领导,来到重医附一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看望科室创始人林尚清教授。
这趟行程,对这位年轻医生触动极大。因为通过林尚清,他了解到从上海来的老前辈们辛苦创建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附一院的故事。
1958年10月,在上医附属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的林尚清受到时任中山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黄家驷教授的委托,来到重医附属综合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建胸心外科。
那时,刚刚成立的胸心外科仅有5张病床,医护人员和胸心外科专职人员严重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林尚清不仅要解决各种难题,还得独自承担门诊、病人接诊、手术和教学等工作,任务繁重。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林尚清还在不断探索心脏手术的规律和经验。为了能够顺利开展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他进行了上百次动物实验,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按照医院规定,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必须要在动物身上成功实施并存活良好后,才能开展临床研究。在那个果腹尚且困难的年代,为了能让实验动物术后尽快恢复,林尚清甚至将自己的口粮省下,喂给实验动物吃。
1960年至1966年,在林尚清的努力下,重医附一院胸心外科相继开展了低温麻醉下心脏直视手术及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的临床应用,走在了全国前列。
王小文还记得,当回忆起创建胸心外科的这段经历时,已经91岁的林尚清感慨万千,他说:“我把全部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重医附一院,献给了胸心外科,来重庆是我最幸福的决定,我从不后悔。”
同样是在1958年,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朱祯卿副教授和我国著名骨科学专家、上医附属华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吴祖尧副教授也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和林尚清一样,他们也是来重医附一院参与科室筹建工作的。
到了附一院,朱祯卿立即组建了神经外科。科室里大到学科建设,小到手术床、手术椅的设计制作,都由他一点点完成。
为了能让老百姓和广大医务工作者了解这门新型学科,建科伊始,朱祯卿就频繁下到基层医院、厂矿农村去进行宣讲,并很快做了第一例椎管内神经鞘膜瘤手术。
吴祖尧到重庆时,正是酷热难耐的夏天,一个大手术下来,他几乎快要昏倒在手术室里;宿舍没电,柴油机只能支撑一盏几瓦的小灯泡微微发亮,每天晚上,吴祖尧都在这微弱的灯光下,熬夜书写教案。
在这样的环境下,吴祖尧咬牙克服着巨大的困难与不适,为菜园坝煤场的一位工人成功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
这些故事,只是西迁老师们创建重医几所附属医院的几个缩影。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上医共向重医调派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400多名。这些老师一直扎根重庆,分布在重医及其附属儿童医院、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第二医院,几十年如一日地开展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为西南地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
|




